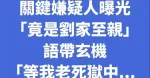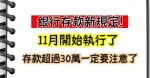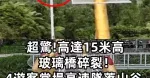2/4
下一頁
沒當過一天皇帝,卻擁有明朝最大帝陵

2/4
▲明世宗像。圖源:網絡
朱厚熜繼位六日,就召集禮官議論父親興獻王的封號及崇祀典禮,揭開了「大禮議」的帷幕。楊廷和等人引經據典,提出嘉靖皇帝應該尊稱孝宗為「皇考」,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在他們眼裡,世宗是接繼武宗,應該歸為武宗一系,所謂「繼統兼繼嗣」。
嘉靖自然不可能同意,難道當個皇帝還要把改認父母?他堅定地說:「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朝臣一百九十餘人次先後抗旨上疏,支持楊廷和的主張。
明世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自己雖然貴為九五之尊,卻被困在一個舊有的枷鎖之中。內閣,本該是備皇帝顧問的機構,如今變成了一個有宰相之實的文官群體。他們以禮法限制皇帝,明世宗甚至不得不以「退位」相要挾。所謂議禮之爭,實則權力之爭。
就在嘉靖孤立無援之際,職銜低微的觀政進士張璁上了一份大禮疏,支持皇帝,主張「繼統不繼嗣」。世宗大喜過望:「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
嘉靖扶持這些中下級官員衝鋒陷陣,很多人被楊廷和利用手中的權力貶官外任,足以證明雙方鬥爭之激烈。同時,嘉靖提拔興王府的舊臣,他們大多是錦衣衛,並不受外廷控制。新的人事結構走向台面,慢慢扭轉了世宗的頹勢。嘉靖三年二月,楊廷和眼見「中興」無望,辭官不做。繼楊廷和之後,大學士蔣冕、毛紀,禮部尚書汪俊,吏部尚書喬宇等先後罷官。
嘉靖三年六月,張璁秘密入京,嘉靖深夜召見張璁說:「禍福與爾共之,如眾洶洶何?」
張璁答道:「彼眾為政耳。天子至尊,明如日,威如霆,疇敢抗者,需錦衣衛數力士足矣。」
此時,皇權依然伸張,張開了它的獠牙。
七月,世宗成功追尊其父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其母「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但是「本生皇考」之外還有一位「孝宗皇考」,這樣便形「兩父」並尊的局面,議禮仍不能結束。
群臣沒辦法了,只能亮出最後一招——「哭諫」。他們聚集在左順門,「撼門大哭」,有人高呼太祖朱元璋,也有人高呼孝宗皇帝,他們渴望這悲痛的聲音可以穿過宮牆,直達皇帝的內心。然而,等待他們卻是廷杖,先後死了十七個人,當然更重要的是對讀書人尊嚴的折辱。在皇權的威嚴之下,所有人都應該低下頭顱。
在殘酷的政治氛圍下,世宗宣布去掉「本生」二字,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自己不再是孝宗之子,明朝帝王的統序也從武宗一脈轉移到世宗一脈。嘉靖七年六月,《明倫大典》發布,鬥爭的勝利果實以官方法令的形式出現。興獻王被「追尊獻皇帝,廟號睿宗」,嘉靖帝的母親蔣氏被尊為章聖慈仁皇太后。
或許在這個時候,明世宗才算真正君臨天下。
對於明朝來說,這也是一個機會,一個清除武宗敗政、革除積弊的機會。
隨著權勢的擴張,明世宗對舊有的弊政進行了多方革新,如裁革冗濫、革除鎮守中官、限革莊田、初行一條鞭法等等。
松林山上的興獻王陵墓,也迎來了改制。明世宗欽定其為「顯陵」,從王墓升格為帝陵。
或許是對於生父的懷念,或許是為了體現自身的正統性,明世宗對顯陵的擴建幾乎貫穿了嘉靖朝始終。直到他去世當年,陵墓的修建也一直在進行,前後斷斷續續竟然持續了四十餘年。雖然相隔千里之遙,他對於陵寢的建設可謂傾盡了心血。
嘉靖十年,明世宗欽定安陸州置承天府,治鍾祥縣,將其出生之地與北京順天、南京應天相提並論。
他命令工匠按照「天壽山七陵之制」大規模改建顯陵,將陵殿門牆都擴建了一番。顯陵的建築沿著中軸線極為有序地布列,寶城、明樓、新紅門、舊紅門、神道、御碑樓、望柱、石像生、欞星門在山水間展開,肅穆的塋城、栩栩如生的文武臣像,彎曲的御河……它們疏密有間,顯示出自然的秀美與人工的精巧。
但由於本身屬於王墓的升格,所以顯陵和明代其它帝陵又有不同之處。
與天壽山七陵不同的是,顯陵在陵區周圍建有高6米 ,寬1.8米,長3600多米的外羅城,呈現出凈瓶狀,與陵宮區圍牆相對,被稱為外羅城。這是世宗的創造,顯陵之後,世宗為自己修建永陵的時候也加建了外羅城一道,這一做法為後世的定陵所仿效,成為明代帝陵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寶城修建成正圓形,這一變化是後期永、昭、定、慶、德五陵寶城變為圓形的轉折點。
朱厚熜繼位六日,就召集禮官議論父親興獻王的封號及崇祀典禮,揭開了「大禮議」的帷幕。楊廷和等人引經據典,提出嘉靖皇帝應該尊稱孝宗為「皇考」,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在他們眼裡,世宗是接繼武宗,應該歸為武宗一系,所謂「繼統兼繼嗣」。
嘉靖自然不可能同意,難道當個皇帝還要把改認父母?他堅定地說:「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朝臣一百九十餘人次先後抗旨上疏,支持楊廷和的主張。
明世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自己雖然貴為九五之尊,卻被困在一個舊有的枷鎖之中。內閣,本該是備皇帝顧問的機構,如今變成了一個有宰相之實的文官群體。他們以禮法限制皇帝,明世宗甚至不得不以「退位」相要挾。所謂議禮之爭,實則權力之爭。
就在嘉靖孤立無援之際,職銜低微的觀政進士張璁上了一份大禮疏,支持皇帝,主張「繼統不繼嗣」。世宗大喜過望:「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
嘉靖扶持這些中下級官員衝鋒陷陣,很多人被楊廷和利用手中的權力貶官外任,足以證明雙方鬥爭之激烈。同時,嘉靖提拔興王府的舊臣,他們大多是錦衣衛,並不受外廷控制。新的人事結構走向台面,慢慢扭轉了世宗的頹勢。嘉靖三年二月,楊廷和眼見「中興」無望,辭官不做。繼楊廷和之後,大學士蔣冕、毛紀,禮部尚書汪俊,吏部尚書喬宇等先後罷官。
嘉靖三年六月,張璁秘密入京,嘉靖深夜召見張璁說:「禍福與爾共之,如眾洶洶何?」
張璁答道:「彼眾為政耳。天子至尊,明如日,威如霆,疇敢抗者,需錦衣衛數力士足矣。」
此時,皇權依然伸張,張開了它的獠牙。
七月,世宗成功追尊其父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其母「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但是「本生皇考」之外還有一位「孝宗皇考」,這樣便形「兩父」並尊的局面,議禮仍不能結束。
群臣沒辦法了,只能亮出最後一招——「哭諫」。他們聚集在左順門,「撼門大哭」,有人高呼太祖朱元璋,也有人高呼孝宗皇帝,他們渴望這悲痛的聲音可以穿過宮牆,直達皇帝的內心。然而,等待他們卻是廷杖,先後死了十七個人,當然更重要的是對讀書人尊嚴的折辱。在皇權的威嚴之下,所有人都應該低下頭顱。
在殘酷的政治氛圍下,世宗宣布去掉「本生」二字,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自己不再是孝宗之子,明朝帝王的統序也從武宗一脈轉移到世宗一脈。嘉靖七年六月,《明倫大典》發布,鬥爭的勝利果實以官方法令的形式出現。興獻王被「追尊獻皇帝,廟號睿宗」,嘉靖帝的母親蔣氏被尊為章聖慈仁皇太后。
或許在這個時候,明世宗才算真正君臨天下。
對於明朝來說,這也是一個機會,一個清除武宗敗政、革除積弊的機會。
隨著權勢的擴張,明世宗對舊有的弊政進行了多方革新,如裁革冗濫、革除鎮守中官、限革莊田、初行一條鞭法等等。
松林山上的興獻王陵墓,也迎來了改制。明世宗欽定其為「顯陵」,從王墓升格為帝陵。
或許是對於生父的懷念,或許是為了體現自身的正統性,明世宗對顯陵的擴建幾乎貫穿了嘉靖朝始終。直到他去世當年,陵墓的修建也一直在進行,前後斷斷續續竟然持續了四十餘年。雖然相隔千里之遙,他對於陵寢的建設可謂傾盡了心血。
嘉靖十年,明世宗欽定安陸州置承天府,治鍾祥縣,將其出生之地與北京順天、南京應天相提並論。
他命令工匠按照「天壽山七陵之制」大規模改建顯陵,將陵殿門牆都擴建了一番。顯陵的建築沿著中軸線極為有序地布列,寶城、明樓、新紅門、舊紅門、神道、御碑樓、望柱、石像生、欞星門在山水間展開,肅穆的塋城、栩栩如生的文武臣像,彎曲的御河……它們疏密有間,顯示出自然的秀美與人工的精巧。
但由於本身屬於王墓的升格,所以顯陵和明代其它帝陵又有不同之處。
與天壽山七陵不同的是,顯陵在陵區周圍建有高6米 ,寬1.8米,長3600多米的外羅城,呈現出凈瓶狀,與陵宮區圍牆相對,被稱為外羅城。這是世宗的創造,顯陵之後,世宗為自己修建永陵的時候也加建了外羅城一道,這一做法為後世的定陵所仿效,成為明代帝陵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寶城修建成正圓形,這一變化是後期永、昭、定、慶、德五陵寶城變為圓形的轉折點。
 呂純弘 • 32K次觀看
呂純弘 • 32K次觀看 呂純弘 • 173K次觀看
呂純弘 • 17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42K次觀看
呂純弘 • 42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舒黛葉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9K次觀看
呂純弘 • 29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18K次觀看
呂純弘 • 18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舒黛葉 • 7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1K次觀看
呂純弘 • 21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