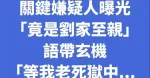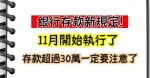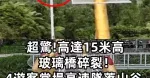3/4
下一頁
真實的後宮生活,每天發12斤肉,妃子不允許串門,每人備一物解悶

3/4
串門不只是「不得」,而是「不能」。你一動,就可能牽動「禁忌」。你走出自己的院子一步,就意味著打破封閉結構、挑戰等級邊界。
而真正能夠自由穿行在各宮之間的,只有一個人——皇帝。
皇帝就是「唯一的流動體」。他臨幸誰,誰就得以「入記」;他召誰,誰就能「出門」。除了他,沒人能自由走動。哪怕是太后,也需要「奉召」才能跨宮而行。
在這座深宮之中,牆不是最可怕的,規矩才是。你一旦違反,你不只是犯錯,而是「動搖皇權秩序」。這在清朝,是政治大罪。
孤獨,是日復一日的折磨
清宮裡,除了規矩、等級、限制,還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東西——寂寞。
一個妃子被選入宮,是榮耀也是禁錮。榮耀是她能住上高門大院,穿上華服金飾。禁錮是她從此不能自由出宮、不能再有親情、友情、愛情,不能愛誰也不能被誰愛。她的全部人生,從進宮那天起,就只剩下一個字:等。
等皇帝翻牌子,等朝賀節日,等升品機會,甚至等死。
所以她們每個人都需要一樣東西——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種「能讓自己不瘋掉的寄託」。
這就是「每人備一物」的由來。
檔案記載,清宮內務府允許妃嬪擁有個人物品——但數量極其有限,多數只能備一樣,最多不超過三樣,且必須登記在冊。她們會選擇什麼?繡花針、琴、書、畫、香爐、小動物,各有偏好,但都指向一個目的:排遣孤獨。
最常見的,是女紅。
很多妃子都拿針線作伴。一塊布、一根針、一雙眼睛,一坐就是一整天。她們不一定要做給誰穿,而是在布上繡風景、繡花鳥、繡詩句、繡回憶。繡線在布上來回穿梭,那是她們唯一能控制的「軌跡」。
曾有清宮檔案記載,一位嬪妃一年繡完一幅《百鳥朝鳳圖》,用掉300多根繡針,磨破4根手指。不是她追求技藝,是她害怕停下來——一停下來,腦子就空了,心也會崩。
也有人喜歡寫字。妃子中識字的不少,尤其旗人家庭出身的,進宮前往往接受過文化教育。於是,她們就拿出筆墨,每天抄經、抄詩、寫家書。宮女說她們「寫字時眼神最亮」,因為那是她們對世界僅存的「想像」。
而真正能夠自由穿行在各宮之間的,只有一個人——皇帝。
皇帝就是「唯一的流動體」。他臨幸誰,誰就得以「入記」;他召誰,誰就能「出門」。除了他,沒人能自由走動。哪怕是太后,也需要「奉召」才能跨宮而行。
在這座深宮之中,牆不是最可怕的,規矩才是。你一旦違反,你不只是犯錯,而是「動搖皇權秩序」。這在清朝,是政治大罪。
孤獨,是日復一日的折磨
清宮裡,除了規矩、等級、限制,還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東西——寂寞。
一個妃子被選入宮,是榮耀也是禁錮。榮耀是她能住上高門大院,穿上華服金飾。禁錮是她從此不能自由出宮、不能再有親情、友情、愛情,不能愛誰也不能被誰愛。她的全部人生,從進宮那天起,就只剩下一個字:等。
等皇帝翻牌子,等朝賀節日,等升品機會,甚至等死。
所以她們每個人都需要一樣東西——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種「能讓自己不瘋掉的寄託」。
這就是「每人備一物」的由來。
檔案記載,清宮內務府允許妃嬪擁有個人物品——但數量極其有限,多數只能備一樣,最多不超過三樣,且必須登記在冊。她們會選擇什麼?繡花針、琴、書、畫、香爐、小動物,各有偏好,但都指向一個目的:排遣孤獨。
最常見的,是女紅。
很多妃子都拿針線作伴。一塊布、一根針、一雙眼睛,一坐就是一整天。她們不一定要做給誰穿,而是在布上繡風景、繡花鳥、繡詩句、繡回憶。繡線在布上來回穿梭,那是她們唯一能控制的「軌跡」。
曾有清宮檔案記載,一位嬪妃一年繡完一幅《百鳥朝鳳圖》,用掉300多根繡針,磨破4根手指。不是她追求技藝,是她害怕停下來——一停下來,腦子就空了,心也會崩。
也有人喜歡寫字。妃子中識字的不少,尤其旗人家庭出身的,進宮前往往接受過文化教育。於是,她們就拿出筆墨,每天抄經、抄詩、寫家書。宮女說她們「寫字時眼神最亮」,因為那是她們對世界僅存的「想像」。
 呂純弘 • 51K次觀看
呂純弘 • 51K次觀看 呂純弘 •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43K次觀看
呂純弘 • 4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35K次觀看
呂純弘 • 35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6K次觀看
奚芝厚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