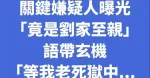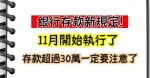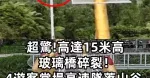3/3
下一頁
三國結束後,魏蜀吳的末代國君和後裔,都去了哪

3/3
上圖_ 劉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字德輿
公元420年,劉裕最終上位成功建立劉宋,而「禪位」的東晉末帝司馬德文卻遠沒有當年曹奐的好運,在被封為「零陵郡王」不久後就連同大批東晉皇室一起慘遭屠戳。而曹虔嗣的表現卻獲得了劉裕的滿意和認可,依然繼續恩待曹家維持待遇不變。直到公元479年,蕭道成建立齊代後才最終取消陳留國。
由此算來,曹魏滅亡後由曹奐「開創」的陳留國竟然歷經西晉、東晉、劉宋兩朝三代,國祚長達214年,是隔壁家「安樂公國」的兩倍有餘,而曹魏本身也才存在了45年,這也創造前朝皇室的一個優待記錄了。
東吳:待遇最差,後代卻起事復國
作為三國中最後一個滅亡的國家,東吳的「存在感」從古到今似乎都是最低的,曹魏雖也常被稱為「篡逆」,但實力最強,又占據著關中、中原一帶的傳統「核心區」,還是由漢獻帝禪讓而來,自認為天命所歸;蜀漢則是劉漢皇室的當然延續,在正統性方面更是當仁不讓。只有東吳這邊似乎什麼都不沾邊,因此底氣不足,就連孫權稱帝也是顫顫巍巍,只敢先稱王,過了10年才稱帝。
而到了東吳滅亡之時,末帝孫皓也和劉禪一樣被押解回洛陽,司馬炎也是熱情款待大擺酒局,同樣是亡國之君,與劉禪的一味討好之態相比,孫皓則表現的更有「可看」性和戲劇性。
面對司馬炎「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的調侃,孫皓立刻從容回懟「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從後面東晉南渡來看碰巧是「一語成讖」);而針對賈充「君在南方,鑿人眼目,剝人麵皮」的斥責,孫皓則反唇相譏「人臣弒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當眾諷刺了賈充曾經參與弒君的惡行,讓賈充當場出醜。
當然孫皓也不忘緩和氣氛和拍拍馬屁,還現場做了一首民謠「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獻給司馬炎。如此一番「騷操作」,充分展現了孫皓的良好口才、應變能力、表演功底外加音樂才華,也讓司馬炎君臣哭笑不得。
孫皓後來被封了個「歸命候」,賞賜給了田畝三十頃,歲給谷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子孫都也安排了官職,結局還算不錯,好歹還能不失「富家翁」的體面和富貴。
只是其爵位只是侯爵,更沒有自己的封國,比起曹奐和劉禪來說可謂相差甚遠,這也似乎印證了東吳存在感最低的事實。孫皓最終42歲病逝於洛陽,並被安葬在著名的邙山,所謂「生在蘇杭,葬在北邙」的說法,能長眠於如此風水寶地,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孫皓雖然在三個亡國之君中混的最差,但他的後代卻比起純「躺平」的曹劉兩家更有野心,並有過起事復國的舉動。《三國志》記載孫皓的兒子多達30多個,其中有兩位都捲入了起事行列。一位是孫充,其在東晉懷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被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的軍閥錢璯擁戴為「吳王」,試圖拉攏人心,但不久之後就被錢璯所殺;另一個兒子孫璠則在8年之後的東晉元帝太興元年(318年)又起兵反晉,結果兵敗被殺。由此可見,即使是在前朝故地,隨著時間的變遷和大環境的變幻,想要復國也是難上加難。
總體來看,魏蜀吳三國末代君主和其後代的結局還算是幸運和不錯的,這與魏晉時期相對寬鬆的政治氛圍和傳統觀念密切相關,當然也少不了被唐太宗李世民稱讚「仁以御物,寬而得眾,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的晉武帝司馬炎的寬厚使然。
而到了後來,末代君王的結局也是越來越慘烈,身死族滅的慘狀接憧而至,像隋煬帝楊廣和南明永曆帝朱由榔甚至都被人分別用練巾和弓弦活活勒死,也許只有南朝劉宋末帝劉准臨死前那句「願生生世世,不復生在帝王家」才能詮釋他們最後一刻的心情吧!
公元420年,劉裕最終上位成功建立劉宋,而「禪位」的東晉末帝司馬德文卻遠沒有當年曹奐的好運,在被封為「零陵郡王」不久後就連同大批東晉皇室一起慘遭屠戳。而曹虔嗣的表現卻獲得了劉裕的滿意和認可,依然繼續恩待曹家維持待遇不變。直到公元479年,蕭道成建立齊代後才最終取消陳留國。
由此算來,曹魏滅亡後由曹奐「開創」的陳留國竟然歷經西晉、東晉、劉宋兩朝三代,國祚長達214年,是隔壁家「安樂公國」的兩倍有餘,而曹魏本身也才存在了45年,這也創造前朝皇室的一個優待記錄了。
東吳:待遇最差,後代卻起事復國
作為三國中最後一個滅亡的國家,東吳的「存在感」從古到今似乎都是最低的,曹魏雖也常被稱為「篡逆」,但實力最強,又占據著關中、中原一帶的傳統「核心區」,還是由漢獻帝禪讓而來,自認為天命所歸;蜀漢則是劉漢皇室的當然延續,在正統性方面更是當仁不讓。只有東吳這邊似乎什麼都不沾邊,因此底氣不足,就連孫權稱帝也是顫顫巍巍,只敢先稱王,過了10年才稱帝。
而到了東吳滅亡之時,末帝孫皓也和劉禪一樣被押解回洛陽,司馬炎也是熱情款待大擺酒局,同樣是亡國之君,與劉禪的一味討好之態相比,孫皓則表現的更有「可看」性和戲劇性。
面對司馬炎「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的調侃,孫皓立刻從容回懟「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從後面東晉南渡來看碰巧是「一語成讖」);而針對賈充「君在南方,鑿人眼目,剝人麵皮」的斥責,孫皓則反唇相譏「人臣弒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當眾諷刺了賈充曾經參與弒君的惡行,讓賈充當場出醜。
當然孫皓也不忘緩和氣氛和拍拍馬屁,還現場做了一首民謠「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獻給司馬炎。如此一番「騷操作」,充分展現了孫皓的良好口才、應變能力、表演功底外加音樂才華,也讓司馬炎君臣哭笑不得。
孫皓後來被封了個「歸命候」,賞賜給了田畝三十頃,歲給谷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子孫都也安排了官職,結局還算不錯,好歹還能不失「富家翁」的體面和富貴。
只是其爵位只是侯爵,更沒有自己的封國,比起曹奐和劉禪來說可謂相差甚遠,這也似乎印證了東吳存在感最低的事實。孫皓最終42歲病逝於洛陽,並被安葬在著名的邙山,所謂「生在蘇杭,葬在北邙」的說法,能長眠於如此風水寶地,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孫皓雖然在三個亡國之君中混的最差,但他的後代卻比起純「躺平」的曹劉兩家更有野心,並有過起事復國的舉動。《三國志》記載孫皓的兒子多達30多個,其中有兩位都捲入了起事行列。一位是孫充,其在東晉懷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被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的軍閥錢璯擁戴為「吳王」,試圖拉攏人心,但不久之後就被錢璯所殺;另一個兒子孫璠則在8年之後的東晉元帝太興元年(318年)又起兵反晉,結果兵敗被殺。由此可見,即使是在前朝故地,隨著時間的變遷和大環境的變幻,想要復國也是難上加難。
總體來看,魏蜀吳三國末代君主和其後代的結局還算是幸運和不錯的,這與魏晉時期相對寬鬆的政治氛圍和傳統觀念密切相關,當然也少不了被唐太宗李世民稱讚「仁以御物,寬而得眾,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的晉武帝司馬炎的寬厚使然。
而到了後來,末代君王的結局也是越來越慘烈,身死族滅的慘狀接憧而至,像隋煬帝楊廣和南明永曆帝朱由榔甚至都被人分別用練巾和弓弦活活勒死,也許只有南朝劉宋末帝劉准臨死前那句「願生生世世,不復生在帝王家」才能詮釋他們最後一刻的心情吧!
 呂純弘 • 51K次觀看
呂純弘 • 51K次觀看 呂純弘 •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43K次觀看
呂純弘 • 4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35K次觀看
呂純弘 • 35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6K次觀看
奚芝厚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