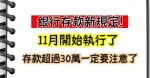3/3
下一頁
女子狀告男子侵犯,魯公當場下令扒光女子衣物,之後真相大白

3/3
他不需要她的傷口,他要她的「清白」,在堂上,她不是受害人,她是被懷疑的女人,她要證明自己貞潔無暇,才配說「我被強姦」,只要有一絲「配合」「沉默」「順從」,她就是「自願」。
這是制度性的冷酷,不是魯永清一人如此,是時代把「貞操」當成法理的基石。
從魯永清到清代:「驗貞」的歷史延續
魯永清的「驗貞」不是孤例。
漢代已設立「通姦」「強姦」兩罪,漢律嚴苛,對女性尤甚,女子被判「奸罪」,甚至施以縫陰酷刑。
到唐代,「驗貞」成了判案重要環節,若女子無明顯傷痕、不哭不鬧,即默認為和姦,貞節是判斷真假的唯一標準。
在清代,這種邏輯更為激進。
清律中,女子一旦告奸,需證明「激烈反抗」,否則,被視為「自污」,更有甚者,需「去衣受刑」,裸身受杖,以證其「非自願」。
刑杖不打在衣服上,必須剝光打,說是懲罰,實為羞辱。
清代《律例彙編》中記載多起「驗貞」案例,多數結局雷同:若女子反抗不力、敘述有誤、行為「不端」,即被判「虛告」和「污告」,杖刑加流放。
女子是否受害,不由司法決定,而由她是否「貞潔」決定,一旦「失貞」,她便不再是清白人。
直到民國,仍有「驗貞」風俗流傳,民國法制雖已改進,但地方執法常沿襲舊制,在一些縣誌中,仍可見「審奸案需脫衣察驗」的記載。
即使在20世紀初,女子告奸,仍需說明「血跡」「撕裂」「尖叫」,否則難以定罪。
現代法治的出現,是對這種羞辱式審判的否定。
刑法第236條規定:強姦罪需多維證據,包括傷痕、物證、證人證言,司法不再依靠「貞潔」判斷真偽,而是依證據認定事實。
對女性的保護,也不再停留在道德層面,「貞操」不再是清白的標準。
隱私權、人格尊嚴、受害人心理,都成為案件考慮的一部分。
扒衣驗貞,被現代法視為嚴重違法,刑訊逼供、人格侮辱、程序違法,均可致審判無效。
而那一樁成都公堂上的「扒衣驗貞」,如今若重演,將構成數項罪名,這是時代的變遷,更是文明的進步。
結語:
她不是在審判中輸掉的,是在制度中被判了死刑。
從她走進衙門的那一刻起,真相已不重要,她的身體、她的貞操、她的沉默,被當成鐵證,不是為了還原事實,而是為了維護一套早已設定好的秩序。
那不是公堂,是一座道德法庭。
魯永清只是那套秩序的執行者,他沒有造出新邏輯,只是順著舊邏輯走到底,他不殘暴,不昏庸。他只是冷靜、有效、符合法條地羞辱了一個女人。
法律未必公正,程序未必中立,真正壓垮她的,不是那四十杖,不是流放,而是整個司法系統要求她「清白」地受害。
她要證明自己不想失貞,而不是證明對方有罪,她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資格。
這不是她的失敗,是那時代的共謀。
如今已無人再提魯永清是「明斷如神」,但他的那場審判,卻留下一道無法癒合的裂口。
那個女子的名字沒人記得了,但她被扒光的那一刻,歷史記住了。
這是制度性的冷酷,不是魯永清一人如此,是時代把「貞操」當成法理的基石。
從魯永清到清代:「驗貞」的歷史延續
魯永清的「驗貞」不是孤例。
漢代已設立「通姦」「強姦」兩罪,漢律嚴苛,對女性尤甚,女子被判「奸罪」,甚至施以縫陰酷刑。
到唐代,「驗貞」成了判案重要環節,若女子無明顯傷痕、不哭不鬧,即默認為和姦,貞節是判斷真假的唯一標準。
在清代,這種邏輯更為激進。
清律中,女子一旦告奸,需證明「激烈反抗」,否則,被視為「自污」,更有甚者,需「去衣受刑」,裸身受杖,以證其「非自願」。
刑杖不打在衣服上,必須剝光打,說是懲罰,實為羞辱。
清代《律例彙編》中記載多起「驗貞」案例,多數結局雷同:若女子反抗不力、敘述有誤、行為「不端」,即被判「虛告」和「污告」,杖刑加流放。
女子是否受害,不由司法決定,而由她是否「貞潔」決定,一旦「失貞」,她便不再是清白人。
直到民國,仍有「驗貞」風俗流傳,民國法制雖已改進,但地方執法常沿襲舊制,在一些縣誌中,仍可見「審奸案需脫衣察驗」的記載。
即使在20世紀初,女子告奸,仍需說明「血跡」「撕裂」「尖叫」,否則難以定罪。
現代法治的出現,是對這種羞辱式審判的否定。
刑法第236條規定:強姦罪需多維證據,包括傷痕、物證、證人證言,司法不再依靠「貞潔」判斷真偽,而是依證據認定事實。
對女性的保護,也不再停留在道德層面,「貞操」不再是清白的標準。
隱私權、人格尊嚴、受害人心理,都成為案件考慮的一部分。
扒衣驗貞,被現代法視為嚴重違法,刑訊逼供、人格侮辱、程序違法,均可致審判無效。
而那一樁成都公堂上的「扒衣驗貞」,如今若重演,將構成數項罪名,這是時代的變遷,更是文明的進步。
結語:
她不是在審判中輸掉的,是在制度中被判了死刑。
從她走進衙門的那一刻起,真相已不重要,她的身體、她的貞操、她的沉默,被當成鐵證,不是為了還原事實,而是為了維護一套早已設定好的秩序。
那不是公堂,是一座道德法庭。
魯永清只是那套秩序的執行者,他沒有造出新邏輯,只是順著舊邏輯走到底,他不殘暴,不昏庸。他只是冷靜、有效、符合法條地羞辱了一個女人。
法律未必公正,程序未必中立,真正壓垮她的,不是那四十杖,不是流放,而是整個司法系統要求她「清白」地受害。
她要證明自己不想失貞,而不是證明對方有罪,她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資格。
這不是她的失敗,是那時代的共謀。
如今已無人再提魯永清是「明斷如神」,但他的那場審判,卻留下一道無法癒合的裂口。
那個女子的名字沒人記得了,但她被扒光的那一刻,歷史記住了。
 呂純弘 • 51K次觀看
呂純弘 • 51K次觀看 呂純弘 •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43K次觀看
呂純弘 • 4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花峰婉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35K次觀看
呂純弘 • 35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3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呂純弘 • 5K次觀看 奚芝厚 • 6K次觀看
奚芝厚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呂純弘 • 19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舒黛葉 • 3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喬峰傳 • 5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舒黛葉 • 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38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11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4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6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
呂純弘 • 22K次觀看